王肖卿:海商法该怎么改
| 时间:2020-10-22 | 编辑:E航网管理员 | 阅读:764 | 分享: |
一、前言
今(2018.10.28~30)年上海海事大学举办的海商法研讨会上,提出一个大哉问,海商法该怎么改?这似乎是个无人可以解答的问题。
台湾的海商法三年前即已透过刚成立的海商法学会,经过正式授权做研究,历时三年弄出一个版本,却似乎没有取得最重要的应用者-航运公司的认同,因而不敢贸然推出。今(2018)年又推出一个新的研究,最近刚接近尾声,奈何也是意见纷歧,难以统合定案。
海商法的重点是货物运送,这点毫无疑义。本次两岸皆启动海商法的修改,虽然没有明说,但估计最大的动力莫如国际新推出的鹿特丹规则。虽然2002推出的旅客运送的雅典公约也才在2014年生效,而维护环境保护一连串推出的2001年燃油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在2017生效、2010年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则跃跃欲出。而修正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Protocol of 1992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1969)与仅香港(不含中国大陆)批准的、修正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Protocol of 1992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1971)也于1996生效后,2000对大陆生效、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和救助公约的1998年修正案也在2000年生效。对这些配合海上环境保护的立法,由于或者已经加入原则一致的1975、1969年旧公约,并无修改的急迫性,反倒是融合以前三个公约原则,更细致、更有条理、配合实务更新过的鹿特丹规则,才应该是这波动念修改海商法的主要原因;英国、欧盟与欧洲其他国家,在1978年联合国推出汉堡规则后,纷纷修改国内的海上货物运送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或是海商法的海上货物运送章,使赔偿标准与原则至少达到威士比修正案的国际普遍接受的赔偿标准,这是上一波海商法的推出与修改的动力。
相较于台湾,大陆在九三年推出的海商法已经相当先进;大量截取了国际公约、国际示范法(modal laws),以及国际惯例的精髓。没有什么较大的问题;台湾则因海商法的推出,始于民国时期的1929年,当时航运不兴,旧观念及疏于注意,使旅客运送竟然至今仍存有:「未」规定部分适用货物运送的离谱规定。因此推论,要不是因应新公约鹿特丹规则的撼动,台湾对沉痾已久的错误规定,都仍可容忍。大陆的海商法则几乎没有改动的急迫性了。
海商法修改是小众间的大事;说是大事,只因海商法是重要的商法之一[1]。惟因只影响小众,关心的人少,或说懂的人也少,短期之内又不致影响国计民生,似又为小事。海商法是公共财,人人得而讨论之,因而众说纷纭,形成一波波的论战,至于孰是孰非?何人得而裁判之?就成了棘手问题。这是本文「海商法该怎么改」的重点。
二、海商法修改的原则
法律修改的方向是政策指导的大方针;小则文字的修订(modify)、大则法条之修改(amend),或者把与实务不符的、在司法上曾经造成误解的、或者容易犯错的地方改正过来(correct),但是修法的目的毕竟是为了修得更好,更实用,让司法判决不致误解海运实务,因此总的来说,政策指示应该只是指导,而不会过度干涉。
作为民商法之一,不外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要目的,是兴利的法规。促进发展则必然干涉越少越好。这个目的却与防弊正好相反;防弊是要让经营产业的人正派经营,不钻漏洞。因此法律的订定又必须不畏繁复、巨细靡遗,让经营者无缝可钻。在这个立场上,过度从防弊的角度出发,或也因此阻碍了产业的发展,尤其具有合同自由性质的海商行为与合同。
海商法的章节中有些章节必须强制,例如对于船舶的规定、对于船员的规定、对于定航班轮运送合同的规定、对于旅客运送合同的规定、港内拖带与海上保险的合同规定等。在船舶的规定上,应该维护司法公正及公权力的尊严。对运送合同,代表合同性质的船票、海运提单、港内拖带及保险合同,为保障合同相对方、经济弱势方的权益,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目的上,需要谨慎、合理、且巨细靡遗订定强制规定。海商法章节中的船舶租用、海难救助,则不外以尊重双方双务合同的合同自由,海商法只做原则性订定就可以了,如此使当事人有更宽广的适用空间。透国国际惯例对于专用术语的定义、解释,也让司法实务能考虑合同内容,做出合理的判断。共同海损是海运长久以来的惯例,其理算当然以尊重惯例,依合同上的理算规则为原则。船舶碰撞、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污染赔偿责任限制、时效等规定,则应考虑海商法的国际性、贸易自由与船舶之航行自由,配合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订定,使经营者更方便走向国际。这样得以推广国内海商法之国际认同与适用,更奢侈一点想,也利于吸引使海商法成为合同准据法,以及以本地做为涉外事件的司法诉讼地点与仲裁的点的选择。
三、国际公约对海商法的影响
国际公约(convention)与国际示范法(modal laws)、海事惯例,对于海商法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海商行为的制度化,可说从西化而来。西化包括参考的国际公约;以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为例,国际法律委员会(ILA)从比利时出发,以国际间指标性的案例,订出第一部共同海损理算规则,转型为国际海事委员会(CMI)后,订定出海牙规则、维士比修正议定书(Visby Amendment)、布鲁塞尔国际特别提款权议定书(SDR Protocol),再经联合国授权,订定汉堡规则、次与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合作,订定鹿特丹规则,这一连串的国际规则制定,除了联合国授权的汉堡、除了联合国与国际海事委员会合作的鹿特丹,海牙一系列(Hague System)的订定,皆出自欧洲,所代表的利益,是船东数量最多的欧洲船东利益。其他的公约也如出一辙;1989的海难救助公约,传递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订定环境保护的特别补偿金(special compensation),这个补偿金却早源于1970年推出的劳氏救助合同。除劳氏外,救助合同种类不少,惟著名的劳氏合同,却是个订定合同的时候,暂时不讲酬报,因此称开放式合同(open form),先付一笔大额保证金,救助不成没有酬报,救助完成再谈酬报。完成救助作业由专业的裁判庭(tribunal),根据参与救难人数、所耗时间、专利技术…等十余项标准,庭讯裁定报酬多寡。而1970的劳氏开放合同(Lloyd’s open form)则早已如是订定;也就是救不成,订约船东须对海难救助者因应减少污染,对环境保护有贡献,仍给予赔偿。私合同推动困难,因此把这一概念转成国际救助公约(International Salvage Convention, 1989),藉由公约推动私合同的做法,就是以上所谓西化的精髓。再举污染赔偿责任限制公约为例,为何要在1969年订定船舶承担民事责任赔偿之后,1971年再追加一个由油货进口商承担的基金公约?目前甚至基金有凌驾民事责任赔偿的作用?国际上大量进口油货的国家有哪些?又不能就近由油管输油,数量庞大、以船舶海运运油货进口的油货商分布在哪些国家?澄清这些问题,便不难了解这些国际公约制定的公目的与私目的。因此海商法如果完全参照对本国不利的国际公约,无异助长公约藉由私合同的邃行无阻。
反过来说,无论主导时的初衷为何,无论主导的是哪个国家,只要订定出来的国际规则,对本国的航运生态有利,对航运与海商发展有利,即使反对者众、即使批准公约的国家不多、即使公约尚缺乏实用验证,海商法的拟定却仍可不顾公约负面阴影,选择参照。商人可以短视,立法却必须前瞻。这也是海商法在选择认同国际公约时,不得不注意之处。
又若干国内法,有要求强制适用于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合同的[2],亦有透过其专用合同的广泛适用,因以推广适用于每份合同[3],若因此选择移植该国内法纳入海商法,恐怕造成紊乱。例如认为英国海上保险法订得好,便欲引入该法于海上保险章;惟在英国,海上保险法之历史及内容足以涵盖保险法,但如台湾海商法的海上保险章却只是海商法的一个章,无疑仍应以保险法为根本;保险法已经有的、业已定义之保险专有名词,海上保险章最好尽量不与之冲撞,否则会造成认知大乱。也会引起保险管理机关的反弹。且保险合同与与船舶租用合同一样是双务合同,管制越少越好,有些条文藉由保单订定即可,法律订定亦不宜与合同制造冲突。认为他山之石,得以攻错,实则生态不同、石质玉质也不同,盲目选择反造成凌乱及误导。
四、汉堡规则与鹿特丹规则
汉堡规则如众所周知是代表货方利益的最大化,相对于海牙系列的船方利益最大化,可说没有汉堡,便催生不出鹿特丹。鹿特丹的好处,是船方、货方都被赋予较重的义务;船方的适航性基本义务延长到航程完成为止。货方则赋予申报货物名称、性质,货物包装能承受海上运送之保证义务。船方、货方责任也都同等加重;船方于船员、引水人之疏忽、过失,失去对货损免责的保障。理赔的责任限制亦提高。货方对于货物造成船方的损害,以及货方负责装卸造成对船舶的损害,须课以责任。在两方在责任、义务都同等加重情况下,却也是自有货物运输公约以来,最为公平的公约。这点符合既是出口大国,也是海运大国的国家利益。
鹿特丹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汉堡规则那个漫无边际的实际承运人身分给局限住,限制之后的海运履约方与履约方,大多是从事陆上工作的人;履约方的作业内容包括履约执行收货(receipt)、装货(loading)、操作(handling)货物上下车、堆装 ( stowage) 货物、运送或搬运(carriage)货物、保管( keeping)货物、照料(care)货物、卸货( unloading)或交货( delivery)作业。且1.履约方不是承运人。2.履约方是依承运人要求(at the carrier’s request)或在承运人监督控制下(or under the carrier’s supervision or control)履(约)(执)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依运送合同执行前述义务之人。另排除受托运人、单证托运人、控制方或受货人聘雇之人。其中的运送或搬运货物,为以车辆或其他运送工具搬运货物之人。而海运履约方则指货物送达船舶装货港,以及货物离开卸货港时,进行履约方履约执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义务之工作内容者。并特别说明内陆承运人仅(exclusively)在港区作业时,是海运履约方。由于其定义的工作内容,由于除了在港区内、亦包括介于港区之间,因此推论海运履约方除了港区范围之作业者-即于装货港港区或者卸货港港区内的作业外,亦包括跨港区之作业者,就是不签提单(否则即为承运人),却提供船舶的登记船东(registered owners)与转租船舶的承租人船东(disponent owners)了。港区间之陆路作业亦属海运履约方[4]。且登记船东在运送责任难以厘清时,必须出面负责。无论如何,这些规定对货方都是有利的。鹿特丹规则也订定了承运人与海运履约方应负共同连带责任。而对于履约方,则承运人应代履约方负责。这样厘清责任的规定,港务公司在接受货物的储存与看守、照料上,无疑必须以海运履约方名义,与承运人承担共同与连带责任。海商法如果对于港务公司是否在海运履约的定义中排除有疑义,在不排除情况下,港务公司与承运人依然可以藉由私合同,排除责任。货方则可因此使至少有一个出面负责任之人;不是海运履约方就是承运人出面负责。同时也厘清了长久以来,部分港口之货物必须交由海关仓库或港务仓库先行收货,造成货损或误放后,公务仓库不肯负责之弊病。这点对船方、对货方都有利。
除此以外,鹿特丹还有不胜枚举的优点;例如除了解决了交货给港务机关仓库或海关仓库的是否属于交货的问题。解决了集装箱运输的舱面装载问题,视其为一般运送。解决了船舶发航后突失航行能力的适航性纠纷。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海牙那种举证责任模糊不清、以及汉堡规则举证责任偏颇的、承运人在假设有责任的基础上负责的基础、导正过来。经过乒乓球式的交叉举证,让举证责任有个更明确的规范。确立最小网状责任制的多式联运模式。而多式联运确定由海运公约统合,则确定了。这点值得海运界感激。因为相对于空运或陆运[5],海运承运人的责任是其中最轻的。是对船方承运人十分有利的规定。鹿特丹的少许缺点则可以藉由国内法导正;例如单证托运人的部分,可以在海商法的运送单证部分,就提单内容予以订定强制要求,确认两个托运人名称都必须列名其上,真实的托运人因此不致隐形,公约内的控制权(right of control)因此有个依附,而解决此一货方疑虑。
五、民商与海商-以租船为例之对照
海商法确实是以民法之损害赔偿用语与概念,形成目前的海商体制,但海商行为却绝非民法债权得以比拟。海商行为性质特殊,即一租船,与民法之租赁,性质就大相径庭。以光船租船去类推民法之租赁,则民法定义租赁「称租赁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物租与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合同」[6],即未能涵盖光船租船原貌;光船租船须搭配船员,方得以「使用、收益」,除了转租,租物本身实难以使用及收益。另民法「租赁关系存续中,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赁物之一部灭失者,承租人得按灭失之部分,请求减少租金」[7]。船舶置于承租人管理下,几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之事由」。船身或船机损坏危及航行安全,必须立即进港入坞修理,修毕未经船级协会认可,不得执行租务,租约未曾有「灭失之部分...减少租金」之订定。如因天灾、战争等无法归责,租约自有合同自动终止(Frustration)条款终止合同,几无可「请求减少租金」之可能。民法「承租人应依约定日期,支付租金。无约定者依习惯,无约定亦无习惯者,应于租赁期满时支付之。如租金分期支付者,于每期届满时支付之。如租赁物之收益有季节者,于收益季节终了时支付之」[8]。相较于租船实务,船舶所有人于租金之收取,非但预收,且收租为绝对之权利;实务惯例及租约均有于期前必须收到租金的规定,「须收到」而非仅「由承租人汇出」,即使第三者或银行延误,除非租约另有订定,否则船舶所有人即有绝对之撤回船舶权(Right of Withdrawal),此均见于光船或期租租约。对照民法「承租人租金支付有迟延者,出租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于期限内不为支付,出租人得终止合同」[9],根本没有适用之余地。民法之「租赁」不同于海商之租船,不仅光船租船如此,期间租船亦然,故光船或期间租船如因民法「租赁」之理由称租船,确实难以参照或准用。
另考民法「雇佣」以「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之合同」[10],适用航租或期租亦有困难。船员受雇于船舶所有人,随着船舶期租租予承租人,承租人因此一并「佣」雇船员,惟雇佣究非租约之目标。租船之船员虽有承租人因船员配合加班装卸,而每月给付定额加班费,惟依约须与租金一道拨付船舶所有人,由船舶所有人转交船员,船舶所有人转付或不全额转付,亦属船舶所有人之权利,因船员之雇用,依船舶所有人与船员之雇用合同,承租人亦无权置喙。
对照民法「承揽」,为「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给付报酬之合同」[11]。适用航租或期租合同恐亦有困难,航租运送之船舶所有人,固符合「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但船舶所有人系以其自有船舶「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即运送任务,运送任务之完成,除船舶成本、船员劳务成本外,因租船方式之不同,而面临风险成本之承担不一,无法以「给付报酬」一词涵盖各式租船。另关于期前迟延解约之第503条,「因可归责于承揽人之事由,迟延工作,显可预见其不能于限期内完成而其迟延可为工作完成后解除合同之原因者,定造人得依前条第二项之规定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与航租之规定亦有出入,以「承揽人」为承租人,定造人为船舶所有人,航租合同签订后,装卸时间之控制为船舶所有人收回船舶再利用之唯一方式;故装卸延误,承租人须支付延滞费(Demurrage)补偿船舶所有人。装卸时间较合同之装卸速率缩短,船舶所有人须给付快速费(Dispatch)。这些船、租相对责任之规定,均为海运独有,民法「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之规定,适用租船即有困难。「因可归责于承揽人之事由,迟延工作」,在海运仅船机故障、船速减慢因而延误船期,造成承租人须多付租金,因而合同均有离租条款(Off-hireClause);由承租人以扣租方式表达不满。海商行为适用民法确有左支右绌之困境。期租租船是三种租船中最复杂的,货损责任须由船、租各自负担,几无其他商事行为可堪比拟[12]。
因此可说海商法本身具有独特性、具体性、趋势性与独创性。其独特性;涉外与国际性是其独特性之由来。其具体性;各个章节的海商行为、海商合同,国际早有既定成形的国际规制,不但具体,而且明确。其趋势性;由于国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污染民事赔偿责任公约、油污染基金公约、国际救助公约第14条之赔偿、残骸移除公约、有毒有害物质民事责任公约等国际公约之发展,皆因趋势而来;承运人、操作人、承租人与船舶所有人之责任因此逐渐加重,这都是趋势带动的结果。其独创性;不讳言海事优先权、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共同海损、海难救助、海上保险,不一样的特殊制度都是海运独有、海商独创。海商法可以民商法理论为指导,却必须建立本身的自体性,海商法缺乏自体性,订出来的海商法恐怕难为国际认同。
六、结论-海商法的适用与修改
台湾由于地域限制,全岛水域都是与海相通的水域,因此总则中的船舶,除了依小船管理规则,以吨位排除小吨位船只之适用外,主要指海上航行,以及与海相通水域航行之船舶。因此内河船舶并不像大陆这样,有是否纳入海商法的疑虑,但是海船驶入内河,自仍应适用海商法,这就如同多式联运纳入陆、空一样的自然。纯内河船自应另有内河管理之规定,而不必像海商法般,在若干规定上还需要考虑国际公约、国际示范法与国际惯例。
然而以旅客运送的雅典公约为例,台湾由渔船改装的赏鲸豚船、离岛小客轮,吨位皆已超过小船管理规则的吨位,载客人数亦超过雅典公约的12人以上船舶,适用该公约的客轮规定,由于赔偿金额超越空运的华沙,倘小船亦纳入海商法之赔偿标准,则这些渔船改装的船舶、离岛小客船,恐皆因无力负担而无法经营,唯有走向关门一途。所以即使与海相通,在旅客运送方面,还是得考虑小船公司的经营困难,设法在海商法中区隔开来。
综合以上区段所述,总结如下:
(一)如果改动是必要的,则怎么改不重要,改得好不好才是重点;站在兴利的立场思考,双面合同有关的章节,应赋予较大的契约自由。防弊的立场,只要对于缺乏双务合同、当事人仅持有合同证明(如提单或船票)的部分,配合国际公约,订定强制性规定。
(二)国际公约的选择应以对整体贸易生态、航运生态有利的去做选择。因为这是趋势,配合趋势即大致不易生差错。
(三)民法虽是商事行为的基本法,惟实证海商却大大不同于民商,国际惯例甚至证明完全不同于民商。海商惯例、配合惯例订定的国际法,是海商法不得不尊的软肋。
(四)除非是多式联运的一部份,纯公路、铁路、内河水运,是国内可以完全掌控的部分,不必受制于国际惯例,不属于多式联运的内河船,应可另订规章,不应有是否纳入海商法的考虑。
(五)如果鹿特丹规则的确是本次海商法修改的原动力,则应重行考虑,大胆启用;因其对船方、对货方均有利,举证规定清晰,对司法实务亦有利。且较之前通过的货物运输公约公平,这点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小缺点包括单证托运人、港务公司属于海运履约方,因此不利等考虑,则可藉由海商法之订定,予以调整及制衡。
目前在海商法的涉外适用上,两岸一致,台湾的海商法甚至定在总则的补充法源规定里,符合多数考虑都希望与国际接轨的心愿。大陆则订在涉外章的规定里。因此在大陆听到「用尽海商法」的声音[13]。优先考虑国际公约看似与国内法的民族主义思考相违,但长远看则有利于国内法之走向国际;不但如前述容易推海商法作为合同准据法之路,从而亦易使本地成为司法管辖地点的思考。这些心愿唯有寄望于立法者前瞻眼光了。
[1]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与海商法号称台湾的四大商法。
[2]例如美国的海上货物运送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3]例如英国的海上保险法(Marine Insurance Act)。
[4]例如上海黄埔港区到上海洋山港区的陆路运输,也是海运履约方。
[5]陆运承运人向来所负为绝对责任;对货方无相对要求,亦无免责规定。空运则由于以旅客为主、货运为辅,华沙公约为旅客、行李及货物之公约,因此承运人责任较重。海运之旅客与货物是分别的公约。
[6]民法第421条。
[7]民法第435条。
[8]民法第439条。
[9]民法第440条。
[10]民法第482条。
[11]民法第490条。
[12]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2310号案「若认为其与上海泛成公司有法律关系存在,其应属于海上运送合同性质,非委任合同性质.......」及「上诉人既自陈被上诉人系委托上海泛成公司办理承揽运送货物至智利,则双方间的法律关系,自应适用承揽运送合同关系。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与上海泛成公司间合同,有委托之文义,性质上较接近事务之处理,故应适用委任合同云云,应无可采」。
[13]用尽海商法即海商事件,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序为国际惯例,次为海商法,尽量摒除其他民商法做判决之考虑。
来源:海商法研究中心
-
刚刚!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两公司集团经理层同时换将!
刚刚!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两公司集团经理层同时换将!…查看全文
-
涨价!MSC再次上调北欧和地中海运价!12月15日实施
涨价!MSC再次上调北欧和地中海运价!12月15日实施…查看全文
-
最新!船公司:调整错误申报附加费!每箱高达30000美元!
最新!船公司:调整错误申报附加费!每箱高达30000美元!…查看全文
-
2025年12月5日煤炭价格走向分析
2025年12月5日煤炭价格走向分析…查看全文
-
沿海运价再全线小跌!市场观望情绪持续。沿海、长江、运河基准运价:长江运价不变、运河运价暂稳、油价持平【E航聊运价】第1787期
沿海运价再全线小跌!市场观望情绪持续。沿海、长江、运河基准运价:…查看全文
-
巨轮做美容,“削鼻子”!一年油钱省出一套大别墅!………每天三分钟,知晓航运事--12月05日
巨轮做美容,“削鼻子”!一年油钱省出一套大别墅!………每天三分钟…查看全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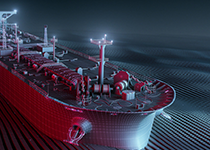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电话:025-85511250 / 85511260 / 85511275
传真:025-85567816
邮箱:89655699@qq.com





